学术交流
研究 | 敏承华 朱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趋势研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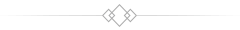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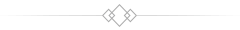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敏承华,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朱 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学、民俗学、口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众号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