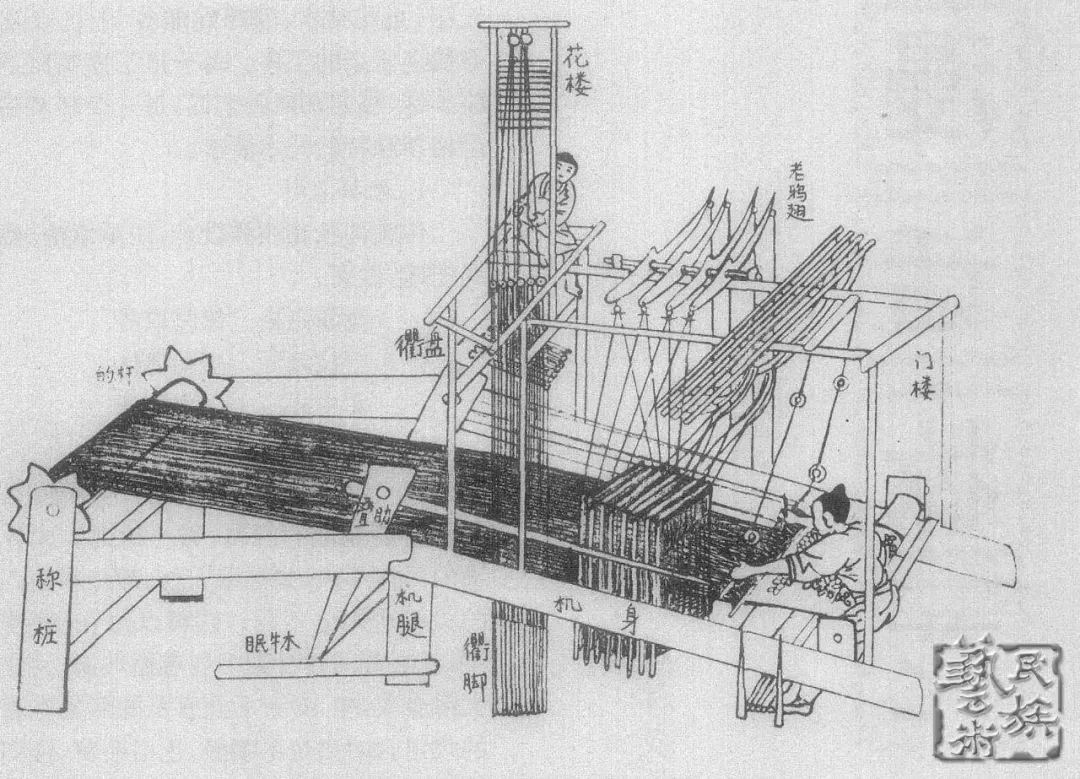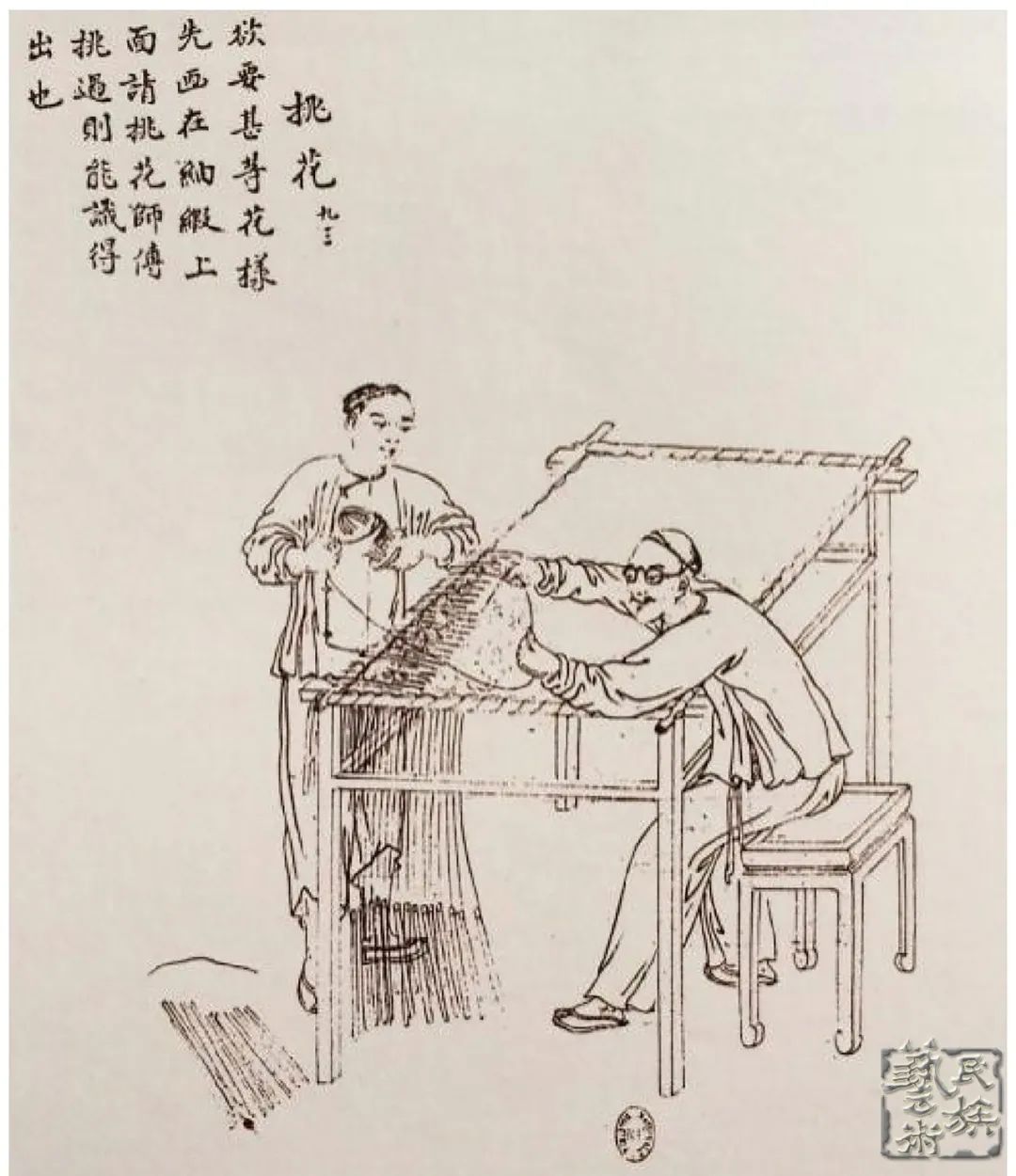研究 | 夏燕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料的艺术史学价值(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应尽快从“行动实践”层面提升至“口述史学建构”上来,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纳入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当中加以阐释。由此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乃属于一种治史与叙史的重要“语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下,共同完成的具有史学意义的“书证”,而这一“书证”的真实性理应得到重视。依此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真正达到兼具思想性、生活性、史料性与可证性,有着另类治史与叙史的价值,让亲历者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认识,为艺术史学研究提供更加生动鲜活的标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经历与珍贵记忆,是丰富和启迪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渊薮。这不仅是将口述史纳入艺术史学叙事移位的需要,还是丰富和建构艺术史学的需要。事实上,有关艺术史学研究的新趋势也表明,专题艺术史中的个案研究业已趋向于向纵深发展。诸如,通过口述史挖掘更多的一手细节史料,重新渗透进艺术史学研究当中,从而在艺术史学的动态研究进程中不断丰富其内涵,树立起现代意识与传统史料学相统一的史学观。换言之,关注口述史的记忆与重现,目的是重新塑造我们的历史认知,强调在与“遗忘竞争”的辨识中,将更多的史料和实证碎片整合为新的素材,辨析出可信度更高的史实给予佐证,理性地面对史学研究关键性素材,即追述“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真实含义。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口述史是对历史研究形成更多元化的解读。对于艺术领域的史料挖掘和积累来说,口述史更为重要,因为艺人的创作经验,往往口述起来更为精彩,是展现更为实在且多元的艺术情境。况且,相较于传统史学所呈现的全像式视角,口述史无疑是微观的。正因为微观,所以更加细腻,由之,口述史触发的历史在场感就更为强烈。自然,这其中也呈现出人的记忆的多样性,这从研究视角来说又是史学文化的特殊灵魂之所在,显示出记忆至为珍贵的财富,从而表明口述史是对人及人群研究的重要靶向,在艺术史研究中以个体观照群体的口述史治史方式,更是研究和揭示艺术史“叙事”新路径的重要参考。